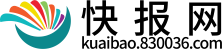
“教父”罗伯特·德尼罗的孙子去世了,年仅19岁。
一个活蹦乱跳的年轻人,怎么会突然暴毙?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在大家的质疑下,法医给出了答案: 他死于药物滥用。
药物滥用,这个你可能觉得很陌生的词,其实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大难题。
在美国,情况尤为严重。
2021年,美国单单因服用芬太尼过量的死亡人数,都超过了枪支与车祸死亡人数的总和。
今年3月5号到6号,得州郊外的社区就发生了5起用药过量事件。
等于你住的小区里, 一天内就有5个人因为药物滥用被救护车拉走。
美国专家预测,再这样下去,从2020年到2029年,至少会有120万美国人死于药物滥用。
全球的数字加起来,就更加庞大到难以估计。
如今,不仅美国的街头偶尔会躺着一个抽搐的年轻人。
连日本也是如此。
我们国家,其实也有一群滥用药物的青少年。
只不过这群人,往往藏在角落里,很难被发现。
全世界药物滥用的主体,几乎都是青少年。
孩子们出于心理压力“嗑药”取乐,甚至把它当成了社交工具和时尚单品。
别以为这只是小孩子之间的打打闹闹,其实已经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社区。
我花了一周时间,潜入滥用药物的群体,发现了令人震惊的现实:
第一,滥用药物的人, 比我们想象中多很多 。可能你身边某个穿着校服挤公交的学生,就在前一晚刚吞过几十片药。
第二,他们的世界里,对药品的评价标准是 “贵不贵” 和 “爽不爽” ,基本不顾对身体的危害。
第三,有人在教他们这样做,并形成了非法的产业链, 只顾谋财,不怕害命 。
在他们的社区里呆了几天,我逐渐摸清了“嗑药”的逻辑。
他们有自己的黑话。
吃药叫“O”,因为药物滥用的英文是“Overdose”。
就像普通人问好是“你吃了没”,他们问好是“你O了没?”。
我们都对成瘾性药物有基本的认知。
知道有管控严格的阿片类药物,包括吗啡、芬太尼、杜冷丁等。
还有比较常见的止咳糖浆和甘草片。
但我们的认知比起这些药物成瘾的孩子来说,还是过于「浅薄」了。
孩子们吃的药,基本上具备两个属性: 便宜和成瘾性。
如果再加上一个特点,就是 “药片比较好咽“ 。
他们的世界里,有两种当饭吃的药。
右美沙芬,昵称“小美”。
原本的作用是治疗咳嗽,但在药物成瘾者的眼里是“一次吃至少十片,可以释放压力”。
盐酸金刚烷胺,昵称“晚安”。
这是帕金森患者的常用药,一旦大量摄入,就会短暂产生幻觉。
“像醉酒一样飘飘然,很快乐”。
他们的圈子里也有自己的测评博主,会替别人尝试“新品”,给出反馈。
比如会不会呕吐、有没有头晕、睡了多久。
我本来对药物剂量没有太大的概念,直到我看见一个人在测评 “美金刚” 。
这种药,我再熟悉不过,是我姥爷治老年痴呆的药。
他是中重度老年痴呆,每次只能吃半片。
一旦吃多,就有可能嗜睡、呕吐、出现幻觉。
但药物滥用群体,每次可以吃上十几二十片。
还夸这种药是“高级版的小美”,因为反应更迅速、强烈。
殊不知,他们所享受的幻觉,都是过量使用药物导致的风险。
我去翻了几篇医学论文,其中药物滥用的案例,都描述得很细致。
每一种药,有不同的反应。
但基本上都会出现恶心呕吐、癫痫甚至呼吸停止,症状已经近似于吸毒带来的副作用。
医生说,药物滥用说好治也好治,说难治也难治。
难治是因为,患者清醒时反应过于剧烈,按都按不住。
好治是因为,治疗的常见手段,就是对患者进行 全麻 。
我看到有医生说,这几年因为药物滥用进医院的孩子,越来越多了。
你可能会觉得,这种孩子一定都是不学无术的“小混混”。
实则不然,很多滥用药物的孩子都生于优异的家庭环境,是家人眼里的好孩子。
因为压力大又无处宣泄,吃药成了这些孩子排解自我的唯一办法。
有个特别经典的例子。
一个男孩叫张洲,来自云南。
他是父母眼中懂事的孩子,却从初中开始偷偷喝止咳水解压。
药物滥用,往往有一个进阶的过程。
从最初的止咳水,到后期的“小美”“晚安”。
从一次吃十几片,再到 八九十片 。
很多孩子慢慢不满足于吃药带来的快感,开始吸毒。
张洲最后,就走到了吸食冰毒的一步,成了彻头彻尾的瘾君子。
等他接受正规的医学干预时,已经瞒着家长滥用药物近十年。
他的身体和神经都受到了不可逆的损伤,输液时一度出现幻觉,非要拔针逃跑,
大好的人生,就这样毁了。
你可能会奇怪,一盒药的价格至少要十几二十块,况且买药也要实名认证,小小年纪的孩子,怎么能有条件一次吃上几十片?
现实是残酷的。
别忘了有句话叫“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
网络买卖,是青少年“嗑药”的主要渠道。
药贩子到他们的社区里发帖,说着黑话,明码标价地卖药。
还可以提供到付、保密发货服务。
他们能从这些不法分子的手上以极低的价格买药,已经不顾收到的究竟是不是假药、有没有危险。
总之只要吃不死,就往死里吃。
并夕夕也是药贩子的主要聚集地。
他们的药品展示界面明目张胆地写着“效果好”“懂的都懂”,生怕钓不来自己的目标客户。
销量处写着刺眼的 “已拼1234件” ,不知道已经赚了多少黑心钱。
更让人忧心的是,从非法渠道买药,已经是比较“高级”的形式了。
实在没钱的孩子,四处寻找购买右美沙芬原料的渠道。
他们说,可以拿原料兑水,当糖浆喝。
买一桶原料,够吃一辈子。
观察这个社区许久,我最深的感悟是。
与其将国内的药物滥用社区比作“阴影之下的角落”,不如说这里是一片日益蔓延的 沼泽 。
这里隐藏着无数只手,紧密地抱团、塌陷、极力吸引别人陷入其中。
他们可能会带着生活中的朋友体验,让整个小团体被药物吞噬。
抑或是在网上邀请别人一起「嗑药」,用激将法劝别人“你是不是不敢吃啊?”,像极了之前恐怖的自杀游戏。
偶尔有人意识到了药物的损害,决定戒掉。
就会有人劝他: “戒个毛啊,晚上再来三排(药)”
还向吃不起药的人提议: 你可以卖肉(淫)、扒车门偷东西,这都是标准操作。
这个深渊巨坑里,堆满了想拉别人下水的恶人。
他们聚集在互联网的阴暗面,仿佛“参与的人越多,我就越隐匿、越安全”。
看到这儿,我终于想明白了,为什么有一个药物滥用者说: 我觉得吃药不仅影响了我的大脑,也影响了我的三观。
因为很多药物滥用者,都是潜在的犯罪者。
他们从青少年开始滥用药物,荒废了学业,影响了身体和大脑的发育,没法体面地拥有一份工作。
可他们需要不低的收入,去负担他们滥用越来越多药物,甚至是吸毒的钱。
最终,只能走向非法敛财的道路。
如今的美国已经初现悲剧的苗头,每年有数以万计的青年人因为服用过量药物去世。
药物滥用,也间接地提升了犯罪率、影响了就业率和就业质量。
印象很深的是,在药物滥用的社区里,有一个格外正能量的帖子。
是一个当老师的人发帖:“我第一次滥用药物,觉得脑子不清楚了,还建议继续吗?”
底下齐刷刷的制止之声,大家都拿出自己的例子告诉他:
“别继续了,会影响记忆力的。”
“我吃了几年,现在人都傻了一半了。”
“千万不要O了,你还得教书育人。”
这一刻,他们集体反对一位老师误入歧途。
可能他们也明白,如果拉他下水,会间接毁掉太多孩子的人生。
当然,我也听到了很多辱骂的声音。
“有钱吃点好的不行吗”
“有你这样的孩子倒了大霉”
“早点死了也不足为惜”
看到这儿,我竟然理解了,为什么有些孩子宁可信任药物,也不肯信任大人和社会。
药物滥用能成为世界性的难题,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们必须承认,它就像一棵盘根错节的树,就算剪秃了所有枝叶,也会换个方向继续生长。
所以吃药只是表象,单纯管控药物一方面会挤压普通人的买药空间,另一方面,也会推动这一群体朝着“阴暗plus”的地步发展。
我们得直面药物滥用背后的几个现实问题:
一是青少年生存环境差,生活压力大。
药物滥用的本质,还是社会问题。
青少年是这个社会初具三观和主体意识的一批人,他们所呈现的行为,就是社会问题的直接反应。
像药物滥用问题背后,就牵扯着社会关怀缺失、药物管理混乱、网络监管缺失等重重问题。
只有从根源解决问题,才能让野草不会“春风吹又生”。
二是青少年认知低,无法对自己的身体负责。
观察滥用药物的青少年许久,我发现他们身上有一个共性:对药物的认知很低,不知道它能带来多么恐怖的伤害。
就像一个人知道火是美丽、炙热的,但不知道玩火能自焚。
我看到一个滥用药物的孩子怒怼大人。
他振振有词地骂: 逮着小孩滥用药物的人能不能先管管长辈酗酒、吃中药啊,你以为你吃饭上瘾就不是瘾啊?
评论区附和: 就是就是,这不是一样的吗?
其实这话在大人看来实在愚蠢,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事情。
国内的青少年从小接受禁毒教育,对海洛因等毒品有一定认知,知道这些东西万万不能碰。
可他们不知道,感冒药和咳嗽药吃得太多,也会让人陷入无尽的疼痛和肾衰竭,直至死亡。
所以,对一个滥用药物的孩子说:“拿这钱买好吃的不爽吗?”
不如直接告诉他,这是你用健康的身体换来的。
而最根本的问题是,很多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无法得到保障。
一位心理医生说,国内药物滥用群体中应该有相当一部分未被诊断的 ADHD (多动症),因为未被诊断干预,发展成了药物成瘾。
所以,除了小部分跟风的人,大部分滥用药物的孩子,可能是真的患有心理疾病。
但治疗心理疾病需要长期的经济支出,很难由一个孩子独立承担。
如果他们长时间被家长漠视甚至鄙视,只能选择和同类抱团寻找群体认同,用伤害身体的方式治愈自己。
事实上,滥用药物的孩子不但被忽视了心理健康,而且连最基本的生活问题都很难保障。
很难想象,在怎样的家庭环境里,一个孩子买回十几二十盒药,每次吃下几十片昏睡半天、迷迷糊糊一周,却没有一位家长发现。
在将这些孩子贬为“无药可救的社会弃子”之前,或许可以先试试,他们的家长是否还 「有药可救」 。
我关注了一个女孩的社交媒体,她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会自残和滥用药物。
在看不到尽头的负面言论里,有一句话戳中了我。
她说: 正向的肯定和扶持,对我来说像是另一个世界的语言。只要我表达出我的阴暗面,能不被人曲解和强行纠正,就已经是对我最好的肯定了。
结合我看到的种种药物滥用的情况,似乎药物滥用这件事对青年人而言,并没有那么高深莫测。
它的本质是青少年的心理需求,而孩子的动机,根本没那么复杂。
就像有个孩子说,他一次次地过量服用“小美”,是因为产生幻觉后,仿佛有人把他带到一个窗明几净的屋子里,很美好,很安心。
究其种种,还是他们在现实中听不见这样美好的声音,无法拥有如此安心的环境。
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居高临下地去面对青少年的心理问题。
社会和家庭,需要给青少年更多人文关怀。
不要光想着如何去“堵”,抱着打地鼠的心态,砸下一个,又冒出一个。
而是得该疏解疏解,该沟通沟通,把“你不可以这样做”,先换成“你为什么这样做”。
站在泥潭外的我们,不要说些冠冕堂皇的话。
站在泥潭里的他们,也别手拉手甘心沉溺,听不进任何人的建议。
当身处阴霾的青少年,不再需要通过药物去体验人生的美好时。
我想,右美沙芬和盐酸金刚烷胺的销量,一定会开始下降。
因为许多依赖药物的青少年,就算远离「小美」,也可以「晚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