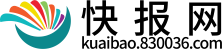
一
我们大院里,曾经有一对夫妇,男的是一位工程师,女的是一位中学老师。他们刚刚搬进大院来的时候,也就三十来岁,我还没有上小学,虽然懵懵懂懂不大懂事,但从全院街坊们齐刷刷惊艳的眼神中,看得出来女教师非常漂亮,男工程师英俊潇洒,每天蝶双飞一样出入大院,成为全院家长教育自己子女选择对象的范本。
那时候,最让全院街坊们羡慕而且叹为观止的是,女教师非常爱吃苹果,每次吃苹果的时候,男工程师都要坐在她的旁边,亲自为她削苹果。削下的苹果皮,都是完完全全地连在一起的,弯弯曲曲从苹果上一圈圈地垂落下来,像是飘曳着一条长长的红丝带。每一次,从宽敞明亮的玻璃窗前,街坊们看到这温馨的一幕时,总能够看到女的眼睛不是望着苹果,而是望着丈夫,静静地等待着,仿佛那是一场精彩的演出,最好总不落幕才好。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他们夫妇有两个孩子,都和我一样前后脚到农村插队,等他们和我一样从农村插队回到北京的时候,他们夫妇已经是快七十岁的人了。那时,女老师已经患上了肝癌,她和两个孩子都不知道,知道的只有她的丈夫。丈夫为她削苹果的时候,手有些颤抖。但是,削下的苹果皮还是完完全全地连在一起,弯弯曲曲从苹果上一圈圈地垂落下来,像是飘曳着一条长长的红丝带。
女教师走得很安详,按照我国传统讲究的五福,即寿、富、康、德和善终,她的一生虽然算不上富贵、健康,也说不上长寿,却占了德和善终两样,应该算是福气之人。送葬的那天,她以前在中学里教过的很多学生来到她家里,向她的遗照鞠躬致哀,有的学生还掉了眼泪。那天,我也去了她家,看见她的遗照前摆着两盘苹果,每盘四个,每个都削了皮,那皮都还是完完全全地连在一起,摆放在苹果的旁边,垂落下来,像是飘曳着一道道挽联。
二
那是五十四年前,我在北大荒过的第一个春节。
全部知青拥挤在知青食堂里。队里杀了一头猪,炖了一锅杀猪菜,为大家打牙祭。队上小卖部的酒,不管是白酒还是果酒,早被大家买光。
这顿年饭,热热闹闹,从中午一直吃到晚上。都是第一次离开家,心中想家的思念便暂时被胃中的美味替代。有人喝高了,有人喝醉了,有人开始唱歌,有人开始唱戏,有人开始掉眼泪……拥挤的食堂里,声浪震天,盖过了门外的风雪呼啸。
就在这时候,菜园里的老李头儿扛着半拉麻袋,一身雪花推门进了食堂。老李头五十多岁,大半辈子侍弄菜地,我们队上的菜园,让他一个人侍弄得姹紫嫣红,供我们全队人吃。不知道他的麻袋里装的什么东西,只见老李头儿把麻袋一倒,满地滚的是卷心菜。望着老李头儿,大家面面相觑,有些莫名其妙。几个喝醉酒的知青冲老李头儿叫道:这时候,你弄点儿洋白菜干什么用呀?倒是再拿点儿酒来呀!
老李头儿没有理他们的叫喊,对身边的一位知青说,你去食堂里面拿把菜刀来。大家更奇怪了。菜刀拿来了,递到老李头儿手里,只见他手起刀落,卷心菜被拦腰切成两半,从菜心里露出来一个苹果。简直就像变魔术一样,这让大家惊叫起来。不一会儿的工夫,半麻袋的卷心菜里的苹果都金蝉脱壳一般滚落出来,每桌上起码有一两个苹果可吃了。
可以说,这是这顿年饭最别致的一道菜了。这是老李头儿的绝活儿。伏苹果挂果的季节,正是卷心菜长叶的时候。老李头儿把苹果放进刚刚卷心的菜心里,外面的叶子一层层陆续包裹上苹果,便成为苹果在北大荒最好的储存方式。没有冰箱的年代里,老李头儿的土法子,也算是一种发明呢。
1978年恢复高考,我考中央戏剧学院,复试的写作,我写的题目是《卷心菜里的红苹果》。
三
从北大荒返城,朋友到家里聚会,是我大显厨艺的机会。兜里兵力不足,不会到餐馆去,只能在家里乐呵。艰苦的条件和环境,常能练就非凡的手艺。那时,在北京吃西餐,只有到动物园边上的莫斯科餐厅,谁有那么多钱!我拿手做的西餐,常被朋友们津津乐道。说来大言不惭,说是西餐,只会两样,一是沙拉,二是烤苹果。
烤苹果,我师出有门。在北大荒插队,回北京探亲,在哈尔滨转车,慕名到中央大道的梅林西餐厅,烤苹果是他家地道的俄罗斯风味。要用国光苹果,因为果肉紧密而脆(用富士苹果则效果差,用红香蕉苹果就没法吃了,因为果肉太面,上火一烤就塌了下来),挖掉一些内心的果肉,浇上红葡萄酒和奶油或芝士,放进烤箱,直至烤熟。家里没有奶油和芝士,有葡萄酒就行,架在篦子上,在煤火炉上烤这道苹果(像老北京的炙子烤肉)。虽然做法简陋,但照样芳香四溢。特别是在冬天吃,白雪红炉,热乎乎的,酒香果香交错,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和感觉。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吃,都觉得新鲜,叫好声迭起,让我特别有成就感,满足卑微的自尊心。
最难忘的一次聚会,是1982年夏天,我大学毕业,专程回北大荒一趟。因我是第一个返城后回北大荒的知青,队上的老乡非常热情,特地杀了一头猪,豪情款待。酒酣耳热之际,找来一个台式录音机,每一位老乡对着录音机说了几句话,让我带回北京给朋友们听。回到北京,请朋友来我家,还是在这个小屋,还是在这个小院,还是做了我拿手的这两道菜,就着从北大荒带回来的60度的北大荒酒,听着从北大荒带回来的这盘磁带的录音,酒喝多,话说多,就是烤的苹果不够多,大家连说没吃够。
四
苹果是一种古老的水果,有几千年的漫长历史。对于苹果的赞美,从古至今在绘画和文学作品中,可以找到许多。从丢勒和克拉纳赫的油画,到欧里庇德斯、莎士比亚,一直到泰戈尔和里尔克以及普列什文,都有描写苹果的诗句。高尔斯华绥写过小说《苹果树》,普宁写过小说《冬苹果》,契诃夫的小说《新娘》也特意把新娘娜嘉要离家出走之地,放在家乡的苹果园中,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小说《盲厨师》中,更是要将莫扎特为临终前的盲厨师演奏的场景,放在了苹果花开的四月清晨。
美国是世界出口苹果最多的国家之一,多是我们现在相当熟悉的蛇果。蛇果英文意思是“美味”,因为那时的蛇果“甜得没有了方向”。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珠海海关前的免税商店,第一次见到这种从美国进口来的蛇果,想全家人都爱吃苹果,特意买了几个带回家,让大家尝尝鲜。谁想,全家人谁也不愿意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甜,关键是太面,有些像我们早就淘汰了的锦红苹果。
我猜想蛇果刚栽培出来时大概不会这样。几千年以来,苹果和人类同呼吸共命运,人类改造着它的命运,也改变着它的口味,苹果的退化是必然的。苹果树,就像一个耕地的牲口一样,被我们使得太狠了,原来的野性渐渐失去,它们的创造性越来越差,滋味当然也就越来越差。
但是,不管怎么说,好苹果还是美味甘甜的,而且,有的还有特殊的别样滋味,让人咀嚼和回味。这样的想法冒出来,是因为看到新出一期的《诗刊》上,有一首写苹果的小诗,作者是我曾经待过的北大荒建三江的一位新人,叫李一泰,因建三江而分外亲切,仿佛他乡遇故知。他写贫苦的母亲用鸡蛋换来一个苹果,用刀切成六瓣,五瓣给孩子,一瓣留给父亲,自己只是舔了舔刀刃上的苹果汁。恰巧这一幕被下班回家的父亲看到——
爹夺过娘手中的菜刀
将自己的那瓣苹果
切成两瓣,塞到娘的手里
娘刚挑亮的那盏油灯
在爹的眼中,瞬间
——模糊了
这首小诗感动了我,因为这样苹果的滋味,也曾经是我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