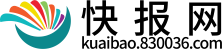
洪峰过后的第10天,斋堂水库水位依旧超汛限约20厘米。水库大坝一侧,泄洪洞的闸门已经关闭,但大坝下方在泄洪时被水流冲刷出的大坑依旧清晰可见。
 【资料图】
【资料图】
“水位已经比最高时降下去8米多了。”又一次登上水库大坝,看着平静的水面,刘波感慨万千。
今年40岁的刘波,是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斋堂水库管理所所长。尽管任现职才一年多,但刘波对斋堂水库却并不陌生,这里是他职业生涯开始的地方。
2007年,刘波大学一毕业就来到了永定河管理处工作,随后被分到斋堂水库管理所。他跟着所里的老师傅们巡视大坝、管护闸门,熟悉这里的每一处水工建筑物。当时的刘波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会在这里指挥全所职工守护水库,迎战洪峰,坚守192小时。
7月29日到8月2日,北京遭遇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强降雨引发洪水,位于门头沟区斋堂镇的斋堂水库水位达到461.56米,创下历史纪录。
7月31日上午,暴雨持续不断冲刷着门头沟山区。作为斋堂水库的“前哨”,清水水文站在测得最后一次数据并回传后不久便与管理所失联。没了观测“前哨”的关键数据,水库的防汛调度怎么办?经验丰富的刘波决定,根据水位变化,反推入库流量。
当天中午,第一次洪峰入库,一时间险象环生。“以前,斋堂水库的最高水位是461.19米,出现在1997年,但那会儿水位是慢慢蓄起来的,不像这次,几乎是眼看着涨。”刘波说。斋堂水库是土石坝,水位过高、上涨过快容易漫顶,有溃坝风险。万一溃坝,后果不堪设想。但下游群众转移需要时间!顶着压力,他们将水库的下泄流量依旧保持在150立方米/秒以下。
按照正常流程,水库的行洪调度指令需由上级部门下达,可此时,斋堂镇的通讯中断了。
“走,到坝上的管理站去!”关键时刻,刘波带领所里的工作人员迅速转移。他知道,管理站里有电台,还有一部卫星电话。不过,就连卫星电话的信号也断断续续。凭着这微弱的信号,刘波接收了指令:可以提闸加大下泄流量。同时,永定河管理处主任陶海军用最大音量和刘波说了三句话:确保水利工程设施绝对安全!确保人员绝对安全!一旦通讯彻底中断,授权你全权处置!“我们一定保住水利设施的安全!我们一定保证自己的安全!”刘波回复。这条信息传送出去后,他们和管理处彻底失联。
陶海军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数次哽咽:“他们不是不珍视自己的生命,但那个时候,只能把下游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摆在自己之前。”
水位涨得太快了,必须下决心提闸加大下泄流量,但为了把对下游的影响降到最低,刘波和同事们采取了逐级提闸的方式。每次先把闸门提高一点,然后观察水位上涨情况,如果水涨速度放缓,就先维持不动,如果水依然涨得很快,再继续提闸,一点点调整。
挑战接连不断。8月1日凌晨,第二次洪峰突袭而至,洪峰流量达到935立方米/秒,需要再次提闸,但市政用电突然中断。“赶紧启动发电机!”刘波立即通知提闸组,同时通过电台试着呼叫属地政府,寻求支援。
“如果有电,我们通过按键操作就能提闸,但是如果发电机出现问题,那就得人工提闸了。”刘波说,人工提闸靠手摇,闸门非常重,需要两人一组配合才行,而且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提闸。但由于道路塌方正在抢修,支援人员无法迅速赶到。
“那时候真是觉得只能靠自己了。”刘波说,他告诉自己,必须要冷静、再冷静,不能慌。“做好人工提闸的准备,万一机械出问题,只能人工上,全力以赴保住大坝。”刘波告诉提闸组。
刘波(左)和同事演示人工提闸。摄影 马岳
万幸,发电机正常运行,刘波和同事们又一次化险为夷。而在这个过程中,斋堂水库的下泄流量始终维持在300立方米/秒,在水库承载能力范围内把下泄流量控制在了最低。
8月1日白天,洪峰过去后,刘波走上水库大坝巡视,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咱们的水利工程设施经受住了洪水的考验,也充分发挥了该有的作用!”
事后,当问起刘波两次洪峰到来时怕不怕,刘波直言:“怕,但也必须顶住,万一溃坝,下游的村庄和群众怎么办?”
在刘波看来,两次迎战洪峰都安然度过,基础在于平时。“咱们的闸门,每年汛期前都要调试启闭,每一处工程都要巡视检查,确保正常。这次强降雨到来前,我们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人员分工明确,发电机加好油保证随时能用……应对洪水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该做的、能做的都做了。”刘波说。
从7月31日8时至8月2日8时,斋堂水库入库洪水总量达7400万立方米,接近100年一遇。而从7月29日降雨开始,到8月6日防洪响应降级,刘波和同事们坚守水库一线奋战192小时,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水务人的职责。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 记者 王天淇
流程编辑:U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