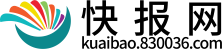
云南的控烟工作走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
8月21日,云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举行《云南省爱国卫生条例(草案)》(下称《草案》)听证会,最新版本的“听证稿”进入公共讨论。多位资深控烟人士指出,草案在控烟部分与国内先进地区有极大差距,且最新的“听证稿”的控烟力度较此前的“征求意见稿”版本还有倒退。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除了未能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止吸烟,《草案》还将指导吸烟区设置的职能交给烟草专卖局,引起多位听证代表的反对。
江苏省扬州市控烟志愿者走上街头,用行为艺术的方式开展“健康生活、远离烟草”主题教育活动,呼吁人们远离烟草。 新华社资料图
今年7月,云南省爱卫办发布听证会公告,招募听证代表和旁听人员。按规定,即将制定的《云南省爱国卫生条例(草案)》属于“重大决策”,其内容是否适当,需要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经过报名、遴选等程序,云南省爱卫办在8月公布了参会名单,包括15名听证代表和12名旁听人员。
据南都记者梳理,15名听证代表中有9人在云南省各级卫生系统工作,至少4人有法律背景。此外,听证会主持人、监察人、决策发言人、听证委员等相关工作人员则大多来自云南省卫健委。南都记者还了解到,包括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在内的多个部门也列席旁听了此次听证会。
今年7月,云南省爱卫办发布听证会公告,招募听证代表和旁听人员。
《草案》共十章六十六条,其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二条与控烟有关,也是《草案》中的主要争议点之一。多位参与听证会的人员告诉南都记者,听证代表的意见集中在控烟相关规定,特别是第二十八条和第二十九条争议较大,约半数的听证代表都就此发表了意见,认为相关规定力度较弱,较国内其他地区同类规定宽松含糊,不能满足控烟工作的要求,也不能达成云南省和国家就受无烟法规保护人口设定的目标。
《草案》第二十八条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控制吸烟(含电子烟)。下列特殊区域室内、室外禁止吸烟:(一)托育机构、幼儿园、中小学校、少年宫、未成年人教育培训机构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公共场所;(二)主要为孕妇、儿童提供服务的机构或者场所,社会福利机构;(三)体育场、健身场的比赛区和座席区;(四)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禁止吸烟区域。
旁听听证会的云南超轶健康咨询中心高级项目经理解玮琳介绍,多位卫健系统的听证代表表示,该规定不符合《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全面禁烟的要求,未纳入工作场所,同时,“控制吸烟”的表述力度不足,应明确为“全面禁止吸烟”。另有一位法律人士直言,与国内其他省市相关条例相比,该规定含糊宽松。
按照国内外的公认标准,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全部应当全面禁烟,削减其中任一部分都会影响整体的控烟力度。而在未能明确全面禁烟的情况下,《草案》仅罗列了部分禁烟区,这可能进一步削弱其效力。例如,《草案》没有明确规定餐馆内禁止吸烟,这使该场所可能成为控烟的一大短板。
长期关注控烟工作的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原主任、新探健康发展中心副主任姜垣分析,控烟执法很难直接进入家庭,在很多工作场所实施也存在问题,因此公共场所的全面禁烟尤为重要。“唯一能推动禁烟的就是公共场所,如果还不全面禁烟,立法有什么用?”她反问。
此外,《草案》虽列举了控烟地区和控烟举措,但未写入对违规吸烟行为的惩罚措施、投诉渠道,这也引起了听证代表对规定能否落地的担忧。
全面无烟立法为何尤为重要?中国占全世界不到19%的人口,吸烟人口却占全世界28%,消耗了全世界44%的卷烟。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统计,中国吸烟人群逾3亿,另有约7.4亿不吸烟人群正在遭受二手烟的危害。
而国内最早执行这一要求的北京已经证明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效果。由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永华团队与常春团队发表的研究显示,《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在2015年实施后,北京市职工因急性心肌梗死和脑卒中(中风)入院人数当期分别即刻下降5.4%和5.6%,带来了显著的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健康收益。
合肥市曙光小学龙图校区的学生在绘制无烟宣传的展板。 新华社资料图
《草案》第二十九条同样争议巨大。第二十九条规定,烟草专卖局应当指导控制吸烟场所的管理者或者经营者应当规范设置吸烟区,并符合下列规定:(一)与非吸烟区有效分隔,避开人员密集区域和主要通道;(二)设置吸烟区标志、引导标志,并在吸烟区设置吸烟危害健康的警示标志;(三)放置收集烟灰、烟蒂等废弃物的器具;(四)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解玮琳介绍,将指导吸烟区设置的权力交给烟草专卖局,引起多位听证代表的反对。现场提出了两个主要观点,其一,烟草专卖局与烟草公司为政企合一的体制,存在利益关系,烟草部门参与控烟并指导吸烟区设置不合适;其二,烟草专卖局不具备相关专业资质,该职能应该交给卫健或疾控等对口业务部门。
“烟草业负责指导全省吸烟区的建立,我们觉得真的是特别的荒唐。”一位熟悉云南控烟工作的人士说。
事实上,前述几个条款在《草案》起草过程中的几次变迁恰好反映了云南控烟工作的幕后博弈与困境。
前述熟悉云南控烟工作的人士告诉南都记者,《草案》初稿参考了国内控烟效果较好地区的经验,整体规定较为严格,得到了北京权威专家的肯定,只是考虑到云南当地政经和社会情况妥协了部分控烟举措,便于落地执行。但在起草过程中,与控烟有关的部分至少经历了三次较大的修改,每次修改都削弱了控烟力度。
对比云南省爱卫办5月公布的征求意见稿和7月公布的听证稿,也可看出削弱控烟力度的趋势。在5月的版本中,控制吸烟地区仍包括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这三类场所,而7月版删除了室内工作场所。5月版仅要求规范设置吸烟区,而7月版则将指导吸烟区设置的职能明确交给烟草专卖局负责。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公共卫生专家和控烟专家普遍认为,设置室内吸烟区并不能起到阻止二手烟的效果。“允许室内部分场所设置吸烟区,这就像是在一块游泳池划分出两个区域,一块允许小便,一块不能小便,可最终游泳池的水都会变脏。”在2020年的一场研讨会上有学者如此比喻。而多份研究也表明,即使是密闭式的吸烟亭,也难以阻挡二手烟外泄,依然会影响其他人群。
基于此,允许设置吸烟区还会引起执法困境。济南市卫健委2021年给人大代表的一份答复中谈道,给室内设置吸烟室“开绿灯”不仅违反国内外法规,有悖于健康至上的社会共识,还违背了科学立法、有效执法的原则。答复还称,重庆、大连设置室内吸烟室,脱离工作实际,不具备可操作性,至今无法出台吸烟室的设置标准、场所责任、执法主体和违法吸烟行为取证等相关管理及执法细则,法规执行几近停滞。
回顾云南《草案》的起草过程,前述熟悉云南控烟工作的几位人士评价为“越改越不行”。在他们看来,云南控烟过去的一大成绩就是在创卫工作中,针对违反吸烟区规范的吸烟区、吸烟亭进行了拆除和改变用途,这些设施之前普遍由烟草业设置,且不能满足控烟要求,《草案》如此规定无异于倒退。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春光小学的学生展示禁烟手抄报。 新华社资料图
南方都市报长期跟踪报道各地控烟举措和无烟立法情况,今年与各地控烟人士、公卫专家交流中的一个普遍感受是,2019年以来,地方无烟立法的阻力愈发增大。
由于国家层面的无烟立法长期“难产”,业内希望推动各地主动出台合格的无烟立法,进而实现对全人群的保护。这一思路促成了北京、上海、秦皇岛等一批优秀案例,这些地区的吸烟率也应声下降。而2019年以后出现的多份地方立法,均在控烟力度上大打折扣,控烟界认为,这与烟草业的干涉有关。
控烟界多次公开表达担忧,长此以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的到2030年,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的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详见:中国卷烟产量逆势上涨,专家担心控烟承诺难以实现)
在这一背景下,产烟大省云南的控烟阻力更是明显。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云南烟叶种植面积达到全国的40%,卷烟产量高居全国第一,吸烟率同样高企。“云南的烟草太强了,”姜垣介绍,此前在云南开展控烟相关的培训、宣传等活动,均会受到当地烟草业的影响,一些活动甚至要事先知会烟草业。前述熟悉云南控烟工作的几位人士也谈及类似的案例,一些控烟活动曾因烟草业的介入而被中间叫停。
但与现状相对应的是,烟草重镇云南曾经是国内率先启动控烟的省份之一。南都记者了解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5年批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后,云南卫生系统很快就跟进实施中央转移支付项目,推出一批控烟举措,“抓得特别紧,工作取得成效”。云南的控烟努力也因此受到各方关注,世卫组织就曾在其报告中推广云南降低烟草种植密度的举措。
而在前述熟悉云南控烟工作的几位人士看来,新冠疫情以来的经济下滑,使得地方政府加大了对烟草产业的依赖,控烟工作也随之受挫。他们希望地方政府可以慎重考虑此次立法,写入合格的禁烟条款,“无论从怎样的角度,立法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老百姓的健康和生命吗?爱卫条例的出台不就是预防疾病,延长老百姓的人均寿命吗?”
南都记者多方了解到,面对多位听证代表对控烟条款提出的修改意见,听证会的决策发言人在现场给出了回应。决策发言人表示,出台相关规定时采取了包容审慎的态度,因为控烟涉及多个部门、多个行业、多个领域,对云南来说比较特殊,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稳定等各方面的因素。
决策发言人还表示,会后将和相关部门积极沟通,争取达成共识,满足听证代表提出的合理化意见建议。“我们希望的结果就是这个工作要干,但是不能因为一些蝴蝶效应对整个全国的爱国卫生工作产生一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