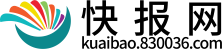
农历七月半,地狱之门开启。鬼魂回到人间,有家的回家,没家的就在四处徘徊;人们点上灯,为自家鬼照亮回家的路。
有很多影视作品都描述过这一天,雾气弥漫、灯火全灭,脖子背后突然感受到一阵凉风,有时月亮还会变成血红色。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鬼节已至,今天,请你听《早期中国的鬼》的作者蒲慕州聊“鬼”。我们从小到大听到的那些或恐怖、或好笑的鬼故事,如何反映人类生存状况,构建出一个理想世界?
*本文经授权转自《晚点LatePost》(ID:postlate);
作者:曾梦龙,编辑:钱杨。
不管对“鬼是否存在”持怎样的态度,不可否认鬼的概念已经进入中国文化。现代汉语便是明证,比如见鬼、鬼打架、鬼话连篇,还有鬼斧神工、神出鬼没,甚至幼稚鬼、顽皮鬼、好吃鬼等等当代形容。
“我把鬼的概念看作一种历史事实和文化现象。”71岁的蒲慕州今年8月在书房里接受《晚点 LatePost》的视频对话时说。
在两个小时的对话时间里,他的语调、表情和动作变化不大,平静真切地述说那个 “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但又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的鬼神世界。
蒲慕州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大概 30 年前就开始研究鬼,主编过《鬼魅神魔:中国通俗文化侧写》与《重思世界宗教中的鬼》(Rethinking Ghosts in World Religions)两本论文集。今年,他关于鬼的首部专著《早期中国的鬼》(Ghosts and Religious Life in Early China)被译成中文出版。
这本书追溯中国从远古到魏晋南北朝时的鬼观念,并与世界其他文化中的鬼比较,揭示中国文化的特色与人类社会的共通。
蒲慕州认为,很多时候人的活动是从自己的信仰出发的。不管这种信仰是真是假,信仰本身会影响历史、文化发展。如果我们搁置鬼是否存在的问题,转而关注鬼的概念或者信仰体系在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什么样的文化和历史结果,就是一个可以相对客观研究的事实与现象。这也是所谓从外部看信仰,而非从内部看,讨论教义之类的问题。
人终有一死。每种信仰对于人死后都要提出一套看法,比如人死之后还存在吗?如果存在,以什么方式存在,去往何处?因此,蒲慕州觉得,鬼可以看作人们对死后世界的一种想象,是信仰发展的一环。他想探究,是什么样的社会文化环境让鬼的观念存在?这种存在给社会制造或解决了什么问题?鬼与人是什么样的关系与本质?
《早期中国的鬼》里称,翻开现今任何一本关于中国文化的书,我们却几乎找不到关于鬼的记述。最有可能找到此类记述的地方是作为文学体裁的鬼故事,或是讨论民间信仰的著作,但那里鬼的篇幅也不多。鬼是中国文化的阴暗面或隐秘的角落,用难以察觉的方式塑造着外在表现。不了解鬼,就无法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直到今天,“你心里有鬼” 之类的说法,仍是意味深长的中文表达。
蒲慕州称,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尤其近代之前,鬼的概念具有相当大影响力。古代笔记小说中有大量鬼故事,说明社会上有这种需要,也折射出人的价值观。到了现代,各种鬼怪电影流行,说明这种兴趣或者需要并未消失。但由于鬼在各信仰传统中多半是负面形象,被一般人排斥,所以很少有人研究。现有鬼的研究,多是文学研究者分析鬼故事。
“我的研究基本上出于个人对信仰、信念和宗教现象的极大好奇,也希望能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有些贡献,提供一个思考与鬼神信仰相关问题的角度。” 他说。
天上地下的鬼神官僚式想象
公元前91年,汉武帝离开都城长安,前往行宫甘泉宫避暑。在长安,宠臣江充设计在皇宫内挖掘出木偶人,以此作为证据指控太子刘据施展巫术,召唤鬼来伤害皇帝。太子措手不及,由于无法与不在都城的皇帝及时取得联系,为了自保,遂将江充处死,仓促举兵与禁卫军发生冲突。这场被称为 “巫蛊之祸” 的事件最后以太子自杀和数千人死亡而告终。
蒲慕州称,尽管汉武帝沉迷信仰鬼神和精神状态衰弱可能是事件的直接原因,但正如后世常评论的那样,当时整个社会弥漫着信仰鬼、巫术和驱鬼的氛围,很大程度上促成这类事件的爆发。
36年前,蒲慕州就从宫廷斗争角度出发,讨论过巫蛊之祸,觉得要考虑当时的宗教和社会心态才能全面了解这一事件。在写过一些与古代信仰有关的著作后,他开始重新思考巫蛊之祸,将于今年底出版新书《汉唐的巫蛊与集体心态》。
“虽然是政治事件,但是事件背后有信仰巫术的社会心态。我这本书写到唐为止,宋以后用巫蛊作为政治斗争的借口就比较少了,虽然下蛊在民间还有传说。” 他说。
这种对鬼的信仰在秦汉时期非常普遍。比如秦始皇信任的方士卢生主张,若要让仙人降临,就要驱除恶鬼;宠幸的妃子王夫人死后,汉武帝请方士少翁召唤王夫人的鬼魂,并确信他在夜里帐幕上看到远远的人影就是王夫人;东汉时期,每年年底都会在首都举行驱除邪鬼的仪式,称为 “大傩”。
《大傩图》,故宫博物院。
蒲慕州觉得,驱鬼行为背后的宇宙观非常有趣。这些恶鬼虽然对人类充满恶意和危险,但却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它们可以被暂时地驱逐出人间,但似乎没有办法一劳永逸地消灭。因此,年复一年,季复一季,驱逐它们的需求反复存在。
公元94年,汉和帝下诏,将每年6月的伏日定为全国性假日。伏日是万鬼出没的日子,因此一整天,人们都被命令关上大门,不事任何生产。有学者认为,伏日就是后来农历七月中旬庆祝的中元节的早期版本。
蒲慕州认为,伏日和中元不一定有关系,但是有关万鬼出没的概念确是很有意思的共通之处。中元节最早可能只是古代农业活动的一个节点,要到南北朝之后,佛教的盂兰盆节(梵文音译,意为解救倒悬苦难)开始受重视,又和道教仪式(如做法事,超度亡魂)合流,才逐渐转变为所谓的鬼节。
“在现代,鬼节的存在一般都视之为民俗信仰。从正面角度来看,它和中国传统儒家所谓慎终追远的精神也有契合之处。只是它由照顾一家的祖先扩大到照顾整个社群的先人,包括各种孤魂野鬼,也颇有墨家兼爱的精神。等于儒、释、道、墨搞到一块,很合中国老百姓的胃口。” 蒲慕州说。
曾侯乙彩棺上的神怪图像。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战国早期的礼乐文明》,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 28 页。
秦汉时期,大一统帝国建立,官僚系统发展完备,对鬼概念的发展也产生影响。蒲慕州称,人们对灵界、阴间或天界开始存在一种官僚系统式的想象,并在随后几千年里成为中国人宗教想象历久不衰的模型。
他解释,人对死后的想象多半是根据活着时的生活环境来的。官僚化的阴间是官僚化社会出现之后的结果,反映了权力关系。不止中国如此,其他古代文明也有类似情况。英国人类学家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写过《帝国的隐喻》一书,提出中国的民间宗教信仰体系是根据帝国的架构来想象的。不论天上地下,都是这样。比如明清的妈祖信仰,皇帝封妈祖为 “天上圣母”,她的存在跟帝国制度有直接对应关系。
再比如,道教基本上就是一个帝国,天宫所有神明按资排序,是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还有民间文化中的城隍,城隍或者说土地公,就是一个城的官僚,对应人间的县太爷或者地方长老,各自属于大的官僚体系中的一部分。受佛教影响,南北朝之后出现十殿阎王,即地下世界的十个主宰,各有称号。这都是帝国组织模式。
魏晋时期的《列异传》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魏国将军蒋济死去的儿子托梦给母亲,说自己 “生时为卿相子孙,今在地下为泰山伍伯(鬼世界的小差吏),憔悴困辱,不可复言”。他希望母亲让父亲去找太庙的孙阿,后面帮忙给自己换个舒适的差事,因为孙阿即将就任泰山令(鬼世界的县令)。
蒋济得知后不信。儿子又托梦给母亲,描绘一番孙阿的身形相貌。妻子由此劝丈夫试一试,验证真伪。果然,蒋济找到一模一样的孙阿。孙阿听到自己要去当泰山令后大喜,答应蒋济的请求。蒋济也重赏了他。没过多久,孙阿去世。一个多月后,蒋济的儿子托梦给母亲,说自己如愿调任为录事(鬼世界负责抄写的小官)。
“20世纪初以来,帝国不复存在,但在民间文化中,仍未能对这种传统信仰架构造成改变,像三太子、保生大帝、开漳圣王,这个大帝那个大帝,这个王那个王,没有什么变化。” 蒲慕州说。
佛、道如何传承和改造鬼概念
1995 年出版《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之后,蒲慕州开始进一步细看中国古代信仰活动中的具体内容。他先是关注道教的神仙与佛教的高僧,后来意识到要了解佛、道两教在中国的发展,需要先了解为两者生长提供养分的文化土壤。
“佛、道传承和改造鬼概念,我认为是一个关键问题。” 蒲慕州说。
道教兴起于汉代,佛教也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它们都利用了在民众中间流行的鬼认知框架推进教业,通过声称可以 “驱鬼” 来获取更多信众。虽然佛、道都宣称自己在世界上伸张正义,但它们对鬼的来源看法不同,驱鬼方式也各有特色。
蒲慕州称,在道教世界中,鬼基本上是人的敌人。人不愿意与鬼互动,但鬼无法被消灭,世间总有无数的鬼需要被驱逐,这样道士们才能被民众不断雇佣。这些鬼,多半是为自己受到的冤屈喊冤。这继承了早期中国的鬼观念,认为人遭遇不公、意外、疾病、战争等非正常死亡,鬼魂才会回到阳间,缠扰活人。
但与早期史料中的鬼相比,道教典籍中鬼的规模和数量之大,反映现实社会的苦难,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鬼似乎主导整个信仰体系。因为汉朝灭亡后,战争、瘟疫等灾难影响数百万人生活,很容易成为道教典籍作者创作的素材来源。
“百万鬼兵戮尽大地的这种描述可能是基于当时的历史现实,或是受其启发。再者,铺天盖地的鬼名表列,生动地描绘了一个被战争和疾病撕裂和摧毁的社会”,蒲慕州在《早期中国的鬼》中写道,“因生灵涂炭,几乎普天之下尽为鬼。不仅人类遭受了惨绝人寰的命运,官邸、旅社、军营、房梁、马车、道路、水井、炉灶、池塘、沼泽等一切世间事物都被毁坏殆尽,变成了鬼”。
大概在六朝时期编著的《太上正一咒鬼经》提供了一份鬼名表:“思想鬼,伏尸鬼,肛死鬼,淫死鬼,老死鬼,宫舍鬼,军营鬼,狱死鬼,惊人鬼,木死鬼,火死鬼,水死鬼,客死鬼,未葬鬼,道路鬼,兵死鬼,星死鬼,血死鬼,斩死鬼,绞死鬼,自刺鬼,恐人鬼,强死鬼,两头鬼,骑乘鬼,车驾鬼,山鬼,土鬼,羌胡鬼,蛮夷鬼,百虫鬼,诈称鬼……当诵是经,咒鬼名字,病即除差,所向皆通。”
念出鬼的名字是道教驱鬼仪式中的一环。神秘的咒语、迷人的音乐、华丽的服饰、夸张的 “禹步”,都是道士驱鬼仪式的经典桥段。禹步是一种古老的仪式行为,在秦代驱鬼文书《日书》中已经出现。它的特征是表演者沿着北斗七星的图样,两脚交替,一前一后地行走。
颜庚的《钟馗嫁妹图卷》局部,创作年代为南宋或元代,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和道教不同,佛教世界的鬼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蒲慕州称,佛教典籍最常提到的是饿鬼。饿鬼并非因饥饿致死,而是在世时犯罪或道德败坏(如贪心、贪财、贪色、欺诈、妒忌、谄媚),被惩罚变成饿鬼,下地狱忍受痛苦。佛教借此劝导人们过正直生活,以免堕入悲惨境地。
但在佛教到来之前,中国人对鬼来源的流行观念,与任何强烈的道德伦理价值观没有必要关系。而且,驱鬼只是一种技术或者仪式,只要学会就可以,和好人或坏人无关。
和道教类似,为了争取信众,佛教也要驱鬼。蒲慕州认为佛教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借着呼唤佛陀和菩萨的名字来礼拜佛陀和菩萨,或是背诵佛经中的驱鬼咒语;二是使用法器或实行一些仪式;三是有大智慧并掌握佛法的僧人可以体现佛陀本人的能力,以他们的现身来驱走恶鬼。
驱鬼行为之外,佛教善于将其制作成故事传播,宣教传经。比如《高僧传》里记载:“仪同兰陵萧思话妇刘氏疾病,恒见鬼来吁可骇畏。时迎严说法。严始到外堂。刘氏便见群鬼迸散。” 这表明佛法精进的僧人即使不施咒,也能仅凭自己的现身就驱走恶鬼。
虽然佛、道在中国的发展,给鬼文化注入道德和权威因素,但蒲慕州揭示了更复杂的面向。他认为,对一般大众而言,咒语和仪式仍是重要的依靠。如果用金字塔比喻,佛、道的信仰体系,最上层是道德性较强的义理,高僧、道士对道德修养要求很高。
而在中下层普罗大众的生活中,道德问题其次,咒语和仪式占较重分量。他们要解决的还是那个古老的问题:生活不如意时,怎么处理?念个咒、烧个香、贴个符,各种仪式活动来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这种心态一直存在,中国到现在都是。人总希望有解决办法,需要外在机制替他解决问题。” 蒲慕州说。
所以鬼神信仰始终有生存空间,但蒲慕州强调,信仰是很主观的东西,也不是非黑即白,更像一个光谱,比如你不顺的时候信 90%,幸运的时候只信 20%,但完全不信也很少。“一个人的信仰是游移的。这也是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一个礼拜去一次教会,重新坚定信仰。”
多姿多彩的鬼故事始于六朝
主题从正义到道德
蒲慕州称,中国社会有两种描绘鬼的方式,一种是必须整治恶鬼,另一种是当人们处于放松或猜疑态度时,通俗小说和故事中出现的鬼更具人性化倾向,越来越多姿多彩,充满异能和奥妙事迹。鬼故事既是娱乐文学、奇观记录,也是人类生存状况的一种反映、构建理想世界的一种尝试。
六朝时期的志怪文学是中国鬼文化发展的关键节点。这一时期,鬼从之前没有多少特质的配角,演变成形象丰富、性格成熟的故事主角。
比如率性的鬼。青州刺史宗岱以驳斥鬼的存在而闻名,一天晚上,一个被宗岱停掉祭祀的地方鬼以书生身份出现在他面前,说要报复宗岱。类似的,阮瞻写过无鬼论的文章。有一天,一个鬼伪装成书生找阮瞻,与其辩论鬼是否存在,但无法获胜,最后只好说自己就是鬼,以结束尴尬场面。“鬼几乎是在自诩合理地捍卫自己的生存权。” 蒲慕州写道。
又如天真简单的鬼。一个顽皮鬼总是将肮脏的东西扔到一户人家的食物中来打扰他们。恼怒的主人最终想出一个计谋,大声说,他才不怕脏东西,但如果鬼拿钱砸他,那他就真的气炸了。鬼听信了,之后就向他扔钱,所以他很快就发了一笔小财。
相似的故事有,宋定伯骗鬼说自己也是鬼,还以新鬼无知为由,诱导鬼说出秘密——鬼怕人的唾沫。到了市集,鬼变成一只羊,宋定伯捉住卖了它,“恐其变化,乃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
蒲慕州称,这些故事可能反映人比鬼聪明的心态。即使在今天,“你在骗鬼” 或 “只有鬼才信” 之类的表达也表明,“鬼比人更容易被骗” 的心态还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这些鬼故事看作批评社会恶习——人有时比鬼更奸诈。鬼的天真、简单性格或许才是真正的人性应该有的。
一项研究表明,六朝志怪一共讲述了23个男子与女鬼结婚的故事,其中只有一个女鬼伤害了一个男人,因为她的丈夫在她死后娶了另一个女人。其余女鬼则基本被描绘成迷人且忠诚的恋人,即便有些男人最终变得忘恩负义。另一项对清代小说中狐精的研究显示,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女狐精或者说女鬼有过风流韵事的男人,个人性格和成就不被提及,表明这些信息对于故事来说不必要。
蒲慕州称,一方面,这可以解释为男性讲故事者的性幻想。风流女鬼不计男人的个人成就、道德品质或社会地位,就无缘无故、毫不掩饰、一心一意地爱他们。这对很难成家的穷书生具有吸引力,“人鬼姻缘解决了他们对于所谓理想婚姻的向往”。
另一方面,这也可反映出相比过往,六朝女性在社会活动中享有较大自由度。因为当时道教的葛洪批评妇女可以自由外出,参访寺庙和朋友家;在街头游荡,唱歌喝酒,直到深夜才归家,甚至在朋友家过夜。这反证了社会现实。
还有,报仇的鬼,比如一个人被某个官员冤死,会以鬼的身份回来报仇。助人的鬼,比如一个男鬼替妻儿修好了被暴风雨摧毁的房子;一个女鬼确保一个穷人家庭每天都有足够食物。待助的鬼,比如一个鬼让一个男人重新埋葬他的棺材,让他可以从监禁中被释放出来;一个女鬼请一个男子报复丈夫新纳的小妾,因为小妾虐待女鬼的孩子。
元代画家龚开的《中山出游图》局部,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鬼的类型多样之外,鬼故事的主题在六朝也有变与不变。“正义” 是中国鬼故事中的经典主题。早在先秦时期,杜伯就是著名的鬼魂,警告着不依公义行事的统治者。
周宣王杀了无罪的臣子杜伯。三年后,周宣王会合诸侯在圃田打猎,猎车数百辆,随从数千人,人群布满山野。正当中午,杜伯的鬼魂乘坐白马素车,穿着红衣,拿着红弓,追赶周宣王。他在车上射箭,正中周宣王心脏,使他折断脊骨,倒伏在弓袋之上而死。
六朝时期,这类故事比比皆是。比如晋朝的庾亮在一次军事行动中,以行为不当和阴谋叛乱的罪名将陶侃的儿子陶称处决。已逝的陶侃被公认为正人君子,庾亮则是声名狼藉的权臣和外戚。陶侃的鬼魂出现,对庾亮说:“老仆举君自代。不图此恩,反戮其孤。故来相问,陶称何罪。身已得诉于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寝疾。八年一日死”。
蒲慕州认为,庾亮之死的故事说明,在大众心目中,讲故事者和听故事者如何集体支持鬼来执行死后正义。而且,看似轻松的故事,与当时知识分子对宫廷政治的关注有着密切关系。
“道德” 是六朝志怪中的新主题。比如南朝的费庆伯回家,看到三个戴着红头巾的侍从。他们对费庆伯说:“长官叫你去。” 费庆伯说:“刚刚我才拜见他回来,怎么还要召见我呢?而且你们经常戴黑头巾,今天为什么戴起红的了?” 侍从答道:“我们可不是阳间的官。” 费庆伯意识到他们是鬼,忙跪拜祈求活命。三个鬼答应换个人捉了交差,让费庆伯四天后置办些酒饭款待,但此事千万不可泄露。
四天后,三个鬼来费庆伯家吃饭。费庆伯觉得,他们吃喝的样子和活人没什么不同。费庆伯的妻子生性多疑,对他说:“这一定是妖怪变来骗你的。” 费庆伯不得已告诉妻子前因后果。不一会儿,三个鬼被鞭打流血,愤怒地站在费庆伯面前说:“你为什么要害我们?” 说完,就不在了。费庆伯暴病,不到天亮就死了。
蒲慕州觉得,这个故事表明,人应该信守诺言,即使对鬼也是如此。它也反映了社会现实,即使是在阴间官僚体系中,腐败不足为奇。但最终,不公义、不道德必遭报应。
除了正义、道德这样的严肃主题,一些鬼故事具有诙谐、讽刺或怀疑意味,娱乐色彩更强。还有些鬼故事成为宗教信仰的传播媒介,展现高僧、道士等控制鬼的能力。
“当时鬼故事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的情节超乎日常想象或者生活经验,能够解决一些日常生活中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它构建理想世界。”
当然,鬼故事的发展和那时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氛围有关。蒲慕州分析道,汉末分裂时代,儒家思想的控制力减弱,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得开放。六朝有着 “清谈” 风尚,文人雅士聚在一起东聊西聊,鬼故事传播开来,后来被收录成书,像《世说新语》里就有很多。还有,佛、道的兴起,产生大量有关鬼神的文字。最后,东汉以来纸张广泛使用,有益于历史和文学作品流传。
他认为,六朝之后,鬼故事越来越丰富,包括唐五代志怪传奇,宋代的《夷坚志》《太平广记》,明清时期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子不语》等等。这些鬼故事的情节、人物、鬼怪等更丰富,雅俗共赏,文学成就更高,但其中的鬼概念和六朝时期没有太大差别,一脉相承。
“扬州八怪” 之一、清代画家罗聘的《鬼趣图》局部,存世有多个版本。
到了现代,许多人接触鬼故事不再是通过文学,而是电影。蒲慕州觉得,鬼片的商业属性更强,中国、东亚和西方都会制作鬼片,如《开心鬼》《画皮》《咒怨》《招魂》等等。但看鬼片的人基本上是追求刺激,跟有的人喜欢看动作片一样。
“鬼故事有趣,但也要看到鬼故事背后引申出来的文化现象。什么样的文化和社会,让这类故事流传?” 蒲慕州说。
通过比较各自的鬼
加深对每种文化的理解
蒲慕州是少数在古埃及和古中国研究领域均有建树的学者,提倡比较视野下的历史研究。他说,这辈子最后一本著作可能是《想象的乐园:古埃及和中国的死后世界》。
在《早期中国的鬼》的最后一章,他粗略比较了古代中国、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罗马的鬼。他觉得,比较能使我们有机会在每个社会中定位出鬼的作用的差异和相似之处,以此更好了解诸多宗教体系的特征,最终强化我们对每种文化的理解。
比如,古希腊的鬼似乎并没有像古埃及人那样,有对死者审判的想法,而这想法在塑造道德意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不像中国人那样,形塑基于阳间创造出来的阴间。古罗马的鬼似乎只有工具功能,而没有承担传递某些特殊信息、道德教化或其他功能的角色。古埃及的鬼和活人世界没有交往,不像中国的鬼跟现实社会有关。
“埃及的鬼不像中国的鬼那样自由,后者可以在世界各地漫游,为所欲为地留下踪迹或捣乱。埃及的鬼和神明的关系毫不模糊,不像中国鬼的行为不可预测。因此,中国的主要宗教体系,无论是佛教、道教还是本土的地方宗教仪式,都热衷于控制鬼,而埃及并非如此。” 蒲慕州写道。
蒲慕州在对话中说,基督教理论上不应该有鬼,世界只有一个上帝,没有其他灵性存在。但后来基督教里也有魔鬼,这是欧洲传统社会中民间信仰的遗留。如果作个比喻,佛、道之所以让中国大众容易接受,是因为它们把中国传统社会中原有的信仰概念包含进去。
基督教也一样,鬼怪、巫术等民间信仰渐渐被纳入其中。比如万圣节其实是万鬼节,来自欧洲的地方信仰。当然,现在万圣节世俗化了,变成娱乐节日;圣诞老人源自北欧民间的神,也不是基督教本来有的概念。
《聊斋全图》残卷,约绘制于清光绪年间,现藏于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这三张图分别是《画皮》《聂小倩》和《续黄梁》。(上下滑动查看)
不同文化中的鬼既有差异,也有相似。蒲慕州认为,鬼因为有未竟之事需要处理,会回来找自己的亲人或者仇人解决。这种想法在许多文化中都很常见。它反映了生者的集体焦虑,寻求解决社群内的冲突,并希望确保世代和平继承,以维持社会稳定。
他解释道,人类社会中间的冲突,到底要怎样才能有效解决?正义在社会中间能不能实现?法律不是万能,冤屈常常发生,所以鬼会回来喊冤。弥补缺陷的一种办法是相信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如果你相信一定会有报应,那你的焦虑感会降低,不满情绪能缓解。
“鬼神信仰,或者宗教文化,处理的就是这类东西。问题不能在一段时间内解决,那就靠信念把它结束。不然怎么办?” 蒲慕州说。
而且值得思考的是,各种文化的信仰有同有异,到底是同比较重要,还是异比较重要?以食物为喻,不同的饮食文化都养活了不同文化中的人,但到底是食物的味道比较重要,还是食物的营养比较重要?
回到 “鬼是否存在” 的问题,蒲慕州认为,这最终是每个人主观认定的结果,但这种主观认定受到文化传统塑造。他个人是否相信鬼神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历史学者,需要研究鬼神信仰如何影响历史和文化发展。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和文化现象。
他觉得,鬼概念的普世性反映了人类这种生物具有的基本心理构成。它的起源和语言、宗教类似,和人类大脑的发展一同发展。我们现在能观察到的情况,只是人类长期发展后最近的一些结果。以前人们解释鬼的概念时,常从心理角度看,主要着眼点在人对未知的忧惧或疑惑。因为疑惑,所以不安,因为不安,所以害怕有事发生,而事情之所以发生,应该是有某种力量、某种东西在发生作用。这种东西可以是神明,也可以是鬼魂。
“不过,这种说法尚不能解释为何人会因为未知产生疑惧。神经生理学家正在研究人脑认知能力的发展和结构,也许未来会有人提出更科学的解释。” 蒲慕州说。
点击图片,立即购买《早期中国的鬼》
内容简介:中国古代有一个鬼的世界,它在广被接受的文化话语体系或宏大叙事中并不明显。然而,这个阴暗的鬼世界一直是中国过往的一部分。想要完整认识中国,洞察历史与人心,就不能不了解鬼。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蒲慕州,采用跨学科的方法,从宗教、历史、社会理论、心理认知等多角度,追溯了从远古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存在的鬼观念;并将中国的鬼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鬼进行比较,揭示每种文化的个体特征。
本书原以英文写作,书名为Ghosts and Religious Life in Early China ,2022 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作者将之前自己关于鬼的诸多研究成果融入一书,内容上化繁为简,叙述上简约流畅,更适合大众阅读。
此中文译稿经作者蒲慕州亲自审定。
——在这里看我们的新书喔(<ゝω・)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