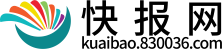
波兰艺术家马乌戈热塔·季茨-克列科特的女儿——艾丽西亚·克列科特,大学毕业,毫不犹豫来到破破烂烂的希腊首都,找到一份参与马戏团青年旅社筹建的工作。
破破烂烂自非贬义。艺术家——乃或深具艺术家视野之徒——素来情有独钟“破破烂烂”的所在。想那冷战谢幕之际,地覆天旋,多少饥肠辘辘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艺术家、音乐家、舞蹈家乃至天知道什么领域的未名之家万里迢迢前去“破破烂烂”的东柏林蚁聚蜂屯。他们穷得好似刚刚遭遇覆舟之难的“廊下派”教主芝诺,既来自多米诺骨牌推倒的东部,亦来自宣称历史终结的西部,无论东西,他们全然看不惯。自由——便是那座城市分给他们最好的礼物。他们占领住宅,占领厂房,占领百货公司,占领历史变迁的离心力抛出的无数空间,只要空着,就去占领——占领自由。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ELLEMEN
第十四届卡塞尔文献展“以雅典为鉴”举办之后,雅典仿佛成了柏林之后的柏林。“新雅典人”大量涌入,他们操着德语、英语、波兰语、俄语、日语乃至汉语,痛惜东柏林电视塔俯瞰的异托邦日趋“正常化”,悄悄地,大张旗鼓地,正头也不回地走上看齐寻常国家政治中心那一副庸暗模样的自毁之路。艾丽西亚便是其中一员。
甫至雅典,我刚刚“喂”了社交媒体一张快照,即被马乌戈热塔隔空擒获。她发现我在雅典,果断留言:自己的女儿也在,你们务须见上一面,至少一面。好吧,既然来了希腊,自然要像黄金时代的古人那样顺服命运。我听从弗罗茨瓦夫发来的指示,经由社交媒体,将艾丽西亚加为好友,写下留言。回话却在次日。我们相约:再过一晚就见。
六月十三日午后,我依照“新雅典人”留下的地址,按图索骥,来到“蒙纳斯提拉奇”以北的“普西里”(Psiri)——一个化腐朽为神奇,化破烂为时髦的街区。除去东正教堂,其余一切本地场所,皆踮起颤颤巍巍的脚尖,向着充担全球生活潮流风向标的《单片眼镜》(Monocle)杂志确认的标准看齐。
翘班的艾丽西亚出现了——她不如母亲那般高大,肤色也不同,许是阿提卡的骄阳晒丢了西里西亚的奶白。吃了没?当然喽,下午四点啦。好呢,那么,去看涂鸦吧。我们“捋”着堪比地震现场的街巷,跨入一片又一片颓墙顽立之地。有那么几个瞬间,我感觉自己回到了“北约”空袭十年之后的贝尔格莱德。穷街陋巷佳作甚多,难容一一赘述。半小时后,艾丽西亚嫌热,直叹披发的福珀斯的矢光炽烈,言外之意,就连海水都被射得沉沉入睡。她建议躲上一躲,拂衣去追瓶中凉。
我们转入一家餐厅,特供希腊葡萄酒,气氛俨若欧里庇得斯笔下的奥德修斯劝酒词:“请看希腊的葡萄做出来的多么神妙的酒,这正是酒神的光荣呀!”侍者跟艾丽西亚挺熟,推荐了两款东地中海岛屿的淳俗勋绩——“传统方法”酿制。不过,它们尚未夺去我对于意大利葡萄酒的偏爱:前者稍显节制;而后者,当属伊壁鸠鲁学说的罗马化,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之后的“快乐”定义。不过,说句玩笑话,也许,问题仅仅出在我口袋里钱少,点得不够贵,尽管窗外的街景远远配不上这份账单。
艾丽西亚晃了晃见了底的酒杯。转场时间到。她的波兰同乡,另一名“新雅典人”,乌尔苏拉·马蒂尼亚克,正在大学区等着我们呢。我打算在西西奥地铁站弄一张周票,可是,无论如何找不到提供此项服务的活人。一只只紧闭的窗口,好似宙斯的臭脸——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第一合唱歌称其“向前朝的神显出一副傲慢的神情”。于是,唯有求诸神经兮兮的自动贩卖机——我就这么与一张五十欧元纸币永别了,它既不退钱,更不吐票。艾丽西亚找来的保安与站长皆毫无办法。与此同时,不想买票的本地人则各施轻功绝活,腾挪身形,纷纷翻越电子闸机的索票关口,仿佛那便是对于社会不公的批判。唯一值得赞叹之处:一名美颊的女孩途径此处,见到学着阿开奥斯人的模样蓄出一头长头发的外国佬无措,认定其囊中羞涩,竟掏出皮夹,相赠车票一张,她又瞧瞧艾丽西亚,一再抱歉并无多余的另一张。
无论如何,我们在看守金苹果的夜的女儿们开始轻吟缓唱之际,赶到了黄昏女神的歌声笼罩的希腊著名无政府主义街区——艾克萨切亚(Exarcheia)。它是这样一类雅典居民的聚集之地——他们反对几百人替几百万人做主。
一伙全副武装的警察正在协和广场地铁站左近晃悠。不远处,尚驻有警车一辆——一辆经过改装的大巴,窗口罩有密密匝匝的金属网,虽说未必防得了枪林弹雨,倒足可抵御砖头石块之类冷兵器。更多警察候在里面,头戴钢盔,手持半透明的防暴大盾。艾丽西亚云:此乃大学区周遭日常景观,雅典的学生比较容易激动,袭承推翻军政府之革命策源地的光荣传统。
我们钻入一片异托邦,介乎柏林十字山与哥本哈根克里斯蒂安尼亚之间。至少外观如斯,其涂鸦密度,更胜乎“普西里”。书店鳞次栉比。此外,还有数目旗鼓相当的咖啡馆和酒吧。以及,鹤立鸡群的公平贸易商店,乃至有机食品杂货铺。可见,此一地界,波西米亚间杂布尔乔亚,主张驳杂,观念的光谱自有其宽度。乌尔苏拉出现了。她高高大大——与艾丽西亚相比,倒更像是马乌戈热塔的女儿,包括突如其来的腼腆——当她听说了自动售票机没收我钞票的故事,却马上掏出身边仅有的五十欧元,命我先用。看得出来,那一张藏于口袋深处,小心翼翼折了又折的纸币,八成是她整周的生活费。
从这些“新雅典人”身上,我仿佛的确望见了世纪之交的柏林,那个已在柏林远去的柏林。
本文原刊载于《ELLEMEN睿士》八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