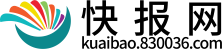
◎韩浩月
 (资料图)
(资料图)
前不久去了一次海边,所住的房间,背靠着大海。到达的时候很晚,没来得及看海的样子,第二天清晨,浓雾散去,透过房间的玻璃窗,可以看见百米之外的海,在懒洋洋地拍打出舒缓的浪花。
因为醒来的比较晚,错过了在房间里看日出的机会,但并不觉得遗憾,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星明星灭,这些都是按照古老规律运转的事物,不会因为一个人多看一眼或少看一眼而怎样怎样,只需知道,在你熟睡的时候,日头的确按时升出来了就好,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早晨金黄的阳光铺满了海面,与你酣睡中的梦境,产生了无形的衔接——睡在海边,与睡在城市当中,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每次到海边,都会在酒店里给朋友写一封信,为的是表达,也为的是纪念。人在海边与自己相处的那些时间,会是很真实的状态,身体内里的混浊,仿佛可以被海风带走,头脑保持着最大程度的清醒,情绪稳定到波澜不惊,因此才可以有效地输出真实的所思所想,这是一次自我校对、自我清洁的过程。
在海边里给朋友写信,总会觉得有很多话想说,很多字想写。那些信写在随手携带的笔记本电脑上,写在酒店的专用信笺上,也写在随便从某处扯出来的几页纸张上。写信不是说话,话语是通过大脑输出,由嘴巴表达,有时候来不及措辞,会有混乱与不准确,但写信无需张嘴,每一个字都是由心而生,那些句子在心里就先排列好了顺序,落在键盘或纸张上的时候,就有了秩序、情感与气质。
但我知道,即便在海边写信,也没法做到言无不尽,那些没法被公开书写的内容,或才是我们的人生真相,但那些被隐藏的生活本质,其实还是在书信流露出来的蛛丝马迹中,留下了入口,写给一位朋友的信,其实是写给许多人、包括许多陌生人在内的信,在书信中,书写者拥有着一种无形的权利——在表达与沉默之间的遥远距离中,他得到了某种自在或者说自由。
海明威一生写过六七千封书信,其中不少是在他居住的古巴海边写的,他说“书信会比我的生命更长久”,他还在信中写道,“假如运气是雨滴,希望你是密西西比河。随后是脸颊贴在悬崖的草上,远眺大海。啊,有多少可看的东西啊。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断了给我写信。是啊,书信是生活的保鲜剂。”写信时的海明威,一点儿也不猛男,他变得如此敏感、脆弱,就如同他写给一位女友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我写信是要让你开心,也因为我孤独。”
在海明威与好朋友菲茨杰拉德的诸多合影中,有一幅他俩站在捕鱼船上的照片(记忆里这幅照片的中间,或许还站着他俩共同的出版人珀金斯),这是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合影,因为照片上海明威的气场中,充满了舍我其谁的主场优势。在古巴,与一位老渔民的偶然交谈,催生了创作《老人与海》的灵感,或也正是这本书的缘故,海明威在古巴住了22年,他还把《老人与海》的原稿和所获的诺贝尔奖章都送给了古巴。
许多作家都痴迷于海,但像海明威这样把海洋当成一种生活方式普及开来的作家,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一个。对于许多中国读者来说,来自西方的海明威,还有来自东方的海子,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海洋想象”的文学脊梁,海明威笔下的海是动的,与海搏斗,其乐无穷,海子笔下的海是静的,“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016年有一部名字叫《海边的曼彻斯特》的电影,非常受欢迎,而被喜欢的理由很简单,它所展示的海边生活,一种被静谧、琐碎、心伤所重重包围的生活,更为贴近当代观众的真实内心,对大海充满掌控与征服欲的时代,早已离人们远去,而对大海的力量感一无所知,甚至对大海视而不见的生活,早已渗透到每个人的生存细节中,每时每刻,都有惊涛骇浪在袭击着普通人的心灵,可呈现在他们的面孔上的表情,却是平静、无奈和悲伤。
《海边的曼彻斯特》的拍摄地,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的名字就叫“海边的曼彻斯特”,在电影公映之后,许多人慕名而来,寻找电影拍摄时出现在大银幕上的画面,在我看来,那些从世界各地不远千里、万里赶来的游客们,其实都在寻找着一种奢侈品,这种奢侈品的名字叫“他人的感伤”,是的,在一个感伤主义重新席卷而来的全球背景下,遥远的他乡,属于别人的感伤生活氛围,竟然具备了一种治愈的效果,而有什么,能比得上海更适合于做感伤的容器呢?
我在海边的时候,一些关键词在脑海中翻滚而过,从众、假文艺、真矫情、浪费时间、荒废时光……这一切与海相关的世俗诠释,都会在某个海浪翻起、海风劲吹的时刻,被瞬间打碎。退休的老年人、失业的中年人、争吵的夫妻、蹦跳着走路的年轻人……他们在海边,身份都被还原成了同一种人,海控制着他们的表情与情绪,海在白天与深夜给他们提供着同一种力量源泉,他们心甘情愿地被某种无法命名的力量操控。
在海边给朋友写的信,通过微信传递出去了,心里想着,隔一段时间,还是要去看一看海。不管怎样,海都像是一位老朋友。你可以不认识他,但他已经认识你很久了。他永远在那儿等你,你在人世间有许多心酸苦楚,他都知道。在海边,你一句话不说,但仿佛心事都已倾诉完。